
第1章
家庭聚会,我和母亲坐在最下首,听姑姑高谈阔论,自家的孩子是多么的优秀懂事,高考足足过了二本线三分。
我看姑姑一边说着,一边拿起白瓷茶杯润了润嗓子,她那双吊眼一直往爷爷奶奶那边瞅。
我往奶奶那边瞧,奶奶脸上的褶子果然皱起来了,两只眼不住地侧目。
父亲昂着头满脸笑容,直言要给纯纯,也就是我的表妹包个大红包。
但是,我却知道父亲摆在桌面下的手肯定攥着拳头。
那拳头一定在抖。
随后,全家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我身上,像是要戳出个洞来。
谁都知道我只考了个三本,这个三本还是母亲花了高额费用请了家教来辅导过的。
我突然想起,考试前一夜,父亲突出的鱼眼泡一样的眼和恶狠狠扼住我脖子的手,让我打了个哆嗦。
回家脱不了一顿打了。
我心里一顿一顿地跳,高领黑毛衣掩盖住的脖子似乎更疼了。
即使是重生回来,肉体的记忆依然让我止不住的战栗。
是的,上一世我是被父亲掐死的。
而现在我回来了——
还没等我缓过劲儿来,姑姑又开口了:
“我记得玲玲和纯纯同岁来着?我出钱,让两个孩子今年暑假一起到上海迪士尼疯一疯。”
垂着头的我感觉左手上方覆盖住一片温热,我抽抽鼻子,熟悉的玫瑰油味钻进鼻腔——是母亲。
“那敢情好啊。不过我们家玲玲已经预定了去香港的票呢。她是姐姐,不如由她带着纯纯去香港的迪士尼?”
一时间全桌沉默,谁都知道母亲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广告设计公司,当初姑姑的工作甚至是母亲介绍的。
要说有前程,谁比谁还不一定……
整个饭桌的气氛诡异起来,母亲攥我的手更用力了。
“鑫啊,你最近工作咋样?”
我听上首的爷爷语音里带着笑问父亲,父亲似乎终于找回了主场话题,变得眉飞色舞,唾沫横飞。
“一切都顺利,董事长给我说明年表现好就升职加薪!”
父亲在的公司是个外资大厂,一年的工资虽然不及母亲的一半,也有个几十万。
“不愧是我儿子,争气!”
我朝奶奶看,她脸上的褶皱“唰”一下抚平了。
明明升职加薪还没着落,奶奶却同父亲成了已经董事长一样神气。
姑姑找了个去洗手间的理由暂时离席,我明白她不仅是针对我,她也看不起我父亲。
当年爷爷奶奶逼她辍学打工养我父亲读书,结果我父亲不争气,只不过读了个高职,多亏遇到我母亲。
我也去了洗手间,在门口却听见姑姑咒骂我爸败絮其中烂泥扶不上墙,爷爷奶奶瞎了眼了把他当个宝。
我抿着嘴,不由自主点了点头。
确实是。
也就爷爷奶奶拿他含嘴怕化,捧在手心怕摔了,只因为他是独子。
一场家宴在一声声客套的恭维中尴尬结束,我和母亲一人一边架着父亲的两只臂膀,醉酒中的父亲仍在口中高声自语。
内容无非就是吹嘘自己在公司里,如何的劳苦功高,如何的备受重用。
跟在后面刚出旋转门的姑姑在一旁添油加醋的讥讽,乐得看我糊涂父亲挥舞两只手臂,把我和母亲折腾的够呛。
我知道她喜欢看我们应接不暇的模样。
父亲两腮嫣红,眼睛半闭半睁,张牙舞爪地像只螃蟹挥舞蟹螯。周围人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我和母亲身上,像是看舞台上的小丑。
我向母亲那边张望,母亲只低着头,掩盖在那头乌发中的耳朵红得惊人。
我听她小声说:“丈夫,咱该回家了。”
我咬住嘴唇,竭力压下把父亲的胳膊甩开的冲动。
母亲总要顾及父亲的面子,而我总要顾及母亲的面子。
面子面子,顾及着面子的人总要打掉牙往肚里吞。
我深知母亲就是这样的人。
我架着父亲的半边身子,他沉得像山,而我像被压在这山下的孙悟空,动弹不得。
我家在小区的最里面,好容易摁着电梯,走廊上的声控灯就亮了起来,父亲还在对自己的功绩滔滔不绝:“公司要没老子,早他妈完蛋了……”
我知道接下来一定会上映全武行,我脑中不由浮现了上一世的情境。
自尊心受挫的父亲拽着母亲的头发,使劲儿往墙上撞,那雪白的墙上留下一点点血色的红梅,透进墙里,铲不掉了。
我这样想着,对架着父亲另一胳膊的母亲哼哼了句:“妈,我有点头疼。”
我故意抽了抽鼻子,母亲脸上浮现出一层担忧,说:“回家吃点感冒冲剂。”
我踌躇一会儿,才斟酌着开口:“我上次喝完了最后一包,家里好像没药了。”
“我去买。”
母亲将肩膀一松,推着父亲上了床,我抬起父亲的两条腿,挪上去,两只胳膊酸痛得呜呜作响。
“啪嗒”门落锁的声音响了。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。灯光罩下来,父亲的影子直直吞没了我。
我看着他因为酗酒而涨红的脸,心脏跳动越来越快,根本刹不住闸。
他会打我吗?或许这一次会跟上一次不一样?
我支走了母亲,他的火气或许没那么大了。
我朝床上不住地望,一点点轻手轻脚地往屋子外面挪。父亲眯着眼,呼呼喘着粗气。我没有出一点声音,他那双细线一样的小眼睛还是对上了我的。明明已经准备好了挨上一顿打来换取证据,我却僵在那里,各种各样的念头都来了。
他会打我!我得跑!
他也不一定会打我,毕竟这是我重生了。
谁说一世一定跟上一世一样呢?
我的脚踩在了棉花上,父亲猛兽出笼般的吼声猛然撞击着耳膜。
“兔崽子,给我站住!”
不能站住!他会揍我的!
快——跑——!
我朝门外一窜,反手关上门,额头麻麻的,太阳穴生疼,心脏像是快要吐到口腔“咔嚓”一下被咬碎一样。
门“咚咚咚”响个没完,我抵着门,从门框上摸到了钥匙,手却是哆嗦着,怎么也插不进锁眼里。
得快点!再快点!不能停下!
我脖子上那一圈青紫和额头同时烧了起来,我死死用尽力气抵住门,两条腿酸溜溜的,没一会儿就面条似的了。
门“哐叽”一声巨响。
父亲走得摇摇晃晃,方向很明确。他的身躯挡住光线,“啪”一个耳光甩过来,我听见了耳朵的嗡鸣,头皮被人整个撕开一样。我眼前一片雪花点,如同老旧的坏掉的电视机屏幕。
我感觉自己的灵魂飘飘忽忽,头脑里只剩下了两句话
——完了!
——要被打死了!
“兔崽子,有本事你给我长长脸……”
父亲的恫吓声像狮吼,我听见自己的脑袋“咔嚓”一声,断了档。
渐渐的,眼前的画面与我六年级的经历重合了。
十几年前,我们一家住在简易楼里。那时候家里没钱,我的衣服都是捡的表哥穿过的衣服,那时候他还活着。
姑姑时常救济我们,我最喜欢她带来的冰糖葫芦,裹着晶莹的糖,上面撒了芝麻,一口咬下去酸酸甜甜。
我几乎是每天都盼着姑姑来我家。
奶奶爷爷对表哥简直当成了个宝,他们会包很多压岁钱,表哥拥有厚厚的一层,我只有一张薄薄的蓝纸。
父亲跟着母亲结婚有了城市户口,计划生育政策执行,反而吃了亏。
父亲骂我是赔钱货,母亲抱着我,他举着拳头砸向我们,“呼呼”生风。
只是因为母亲生不出来男孩,我们都成了出气筒,他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,越喝越上头,我和母亲挨打的频率从一周几次变成了每天都有。
每次母亲弯着腰两只胳膊紧紧搂住我,我都恨不得拿刀捅了他,一了百了。
我的胳膊常年青紫,撸起的袖子都会箍疼我的皮肉,都是母亲拿着蘸了酒精的棉棒一点点给我擦拭开上面的血迹。
直到有一次,父亲一连七天未归,母亲的工资已经是父亲的一倍多。母亲给我做了很多好吃的,还买了田园鸡脆堡的超级套餐。我已经上了初三,住校,一周回一次家,这次放的五一七天是我最舒心的日子。我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,也不想管,只将那句话混着怒气喷出来:
——“妈!你必须离婚!”
母亲闻言怔怔地看着我,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,拍着我的背将我搂进怀里。
没一会儿我就感觉后肩的衣服湿透了,腻乎乎的像一层皮肤。
傻孩子,我听她说,我不能自私,那样你就没有完整的家了。家丑不可外扬。
姑姑曾经专门来过一次,拉着他到别的屋里去谈话,我舔着糖葫芦上的糖,甜滋滋的。可没一会儿,“噼里啪啦”一阵乱响,脆的钝的呼呼啦啦全涌进耳朵,糖葫芦也折了一半。姑姑捂着脸哭着跑出来,父亲没一会儿凸着灯泡眼出来,“哼哧哼哧”呼着气,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还在打颤,咒骂着:“不过是个泼出去的水,还管着我的事儿了!来一次打一次!”
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了表哥的衣服穿。
我抱着头,父亲的拳头一下子砸在我的左肩膀,我眼前冒起了金星。
“那娘们不就是有几个臭钱供我使使,嫁鸡随鸡嫁狗随狗,我是一家之主,好的都应该是我的!”
我随着他的话接了下去。
你那臭小子哥哥体弱多病早死了,也是你姑姑她活该!呸!
我脑子里一会儿全是哥哥,一会儿全是姑姑,奶奶拉着母亲谈的话也冒了出来:
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,他脾气大点,你多担待。”
和奶奶谈完话后,正巧姥姥打了电话来,我躲在门外,透过那一层缝向屋里看。
母亲抹着泪,说话声音除了有点哑外都正常,她就这样边哭边微笑,挂断电话后,将脸埋进了掌心,肩膀一耸一耸的。
世界天旋地转,我分不清日子是何时了,但——
‘呸!’
我在心里暗骂,火气突然冒出来,头皮一阵疼痛,紧接着是钝钝的抽丝剥缕的疼,我眼前一黑。
我替母亲挨了这份打。
我突然有些自豪,随即又担心起来。
母亲回来看到我,会不会又哭了?老东西还会打她。
我不禁祈祷起来:
妈妈,你可千万别回来啊。
那一晚母亲回来的很快,父亲呼呼大睡。
我仍记得母亲颤抖着紫色的嘴唇,那两片唇抖着,在我的脸上胡乱吻着。
母亲睡着了,我将竖在无线充电器上装着充电的手机攥在手心,里面父亲打我的录像完整地记录了下来。
玫瑰花的刺隔着一层塑料膜,红色的带子系成了蝴蝶结的形状,我口袋里还装了一个平安果。今天是周末,还正赶上圣诞节夜。
太阳特别的毒,我却身上冷飕飕的,转身向一边的大乐透彩票站点去了。
上一世我整个学期都是在学校和家中往返,没有住校。
我记得七月六号我拖着行李箱拧开锁,家里只有母亲一人,衣服都被她从衣柜里一件件丢了出来,满地满床全是衣服和散开的鞋袜,她的脸底色是白的,青青紫紫像是涂上的滑稽油彩,我抱着肩膀浑身发冷,转而跑向书房,地上也是一片狼藉,巴掌大的碎纸屑花花绿绿,我才知道那是一张张撕碎的彩票。
也就是那时起,我才知道父亲对彩票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。
投资超过我,期望值也超过我。
那一天吃饭时,母还收到了一条短信,我不知道是什么,但她头一次在我跟前呜呜大哭着冲向自己的屋子。那一晚,她房间里的灯没灭过。
上一世如同我只翻开了一册书的部分,而另外的一部分要用这一世来见识一下。
我买下了7位数的大乐透,等待着周末的开奖。
我隐隐约约觉得,家庭不幸总是关于钱的缘故。
今天是六月十五号,离我被父亲掐死还剩下一个月零八天。
暑假回家的第一天,天气正好,因为昨天刚下了小雨,暑气不是很大。
我拉着行李箱,好似里面有千斤重。
今天妈还会翻来覆去找东西吗?
是因为钱吗?妈应该不缺钱。难道是什么贵重物品?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东西?要不她怎么会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呢?
但如果是钱的话,也好办了。
我拉着行李箱杆子的手攥紧了,手心里全是汗。我抬头望着自家合上的窗帘,深吸一口气进了楼栋。
家里狼藉一片,母亲的牛仔裤是我进房间的第一件拦路虎。我缓缓吐纳一口气。
上一世的时候,我只知道躲避事情。我不想有任何的麻烦事在身上,也不想主动挑起任何事端。但这一次不同,我必须活着。我要活着见到秋季的太阳,我要活着见到以后每一天许许多多的日出日落。
我推开虚掩的门,母亲正跪在地上把衣柜最下层抽屉里的衣服一件件掷出来。
“妈,你在找什么?”
我的嗓子很紧,紧到像一根拉紧的弦,吐出来的声音干涩沙哑,声音也很小。
“没你的事,回屋去。”
母亲仍然埋头翻找着衣服,声音的音色却是和我差不多的。
“妈我和你一块儿找,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快些。”
行李箱的杆子早被我丢下了,发出“嘭”一声闷响,母亲垂着头,我抱住她,她将我推开。
事情有些不对了。我想。
妈从来不会推开我,她虽然严厉,但……
我看她半垂着头,长发挡住了她的脸,我看不清她的表情,但一滴明晃晃的水珠,顺着她西装的衣领滚到胸口。
她哭了。
我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,像被人打了一拳。
妈从来不会在我面前哭,从来不会,从来不会……
我看姑姑一边说着,一边拿起白瓷茶杯润了润嗓子,她那双吊眼一直往爷爷奶奶那边瞅。
我往奶奶那边瞧,奶奶脸上的褶子果然皱起来了,两只眼不住地侧目。
父亲昂着头满脸笑容,直言要给纯纯,也就是我的表妹包个大红包。
但是,我却知道父亲摆在桌面下的手肯定攥着拳头。
那拳头一定在抖。
随后,全家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我身上,像是要戳出个洞来。
谁都知道我只考了个三本,这个三本还是母亲花了高额费用请了家教来辅导过的。
我突然想起,考试前一夜,父亲突出的鱼眼泡一样的眼和恶狠狠扼住我脖子的手,让我打了个哆嗦。
回家脱不了一顿打了。
我心里一顿一顿地跳,高领黑毛衣掩盖住的脖子似乎更疼了。
即使是重生回来,肉体的记忆依然让我止不住的战栗。
是的,上一世我是被父亲掐死的。
而现在我回来了——
还没等我缓过劲儿来,姑姑又开口了:
“我记得玲玲和纯纯同岁来着?我出钱,让两个孩子今年暑假一起到上海迪士尼疯一疯。”
垂着头的我感觉左手上方覆盖住一片温热,我抽抽鼻子,熟悉的玫瑰油味钻进鼻腔——是母亲。
“那敢情好啊。不过我们家玲玲已经预定了去香港的票呢。她是姐姐,不如由她带着纯纯去香港的迪士尼?”
一时间全桌沉默,谁都知道母亲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广告设计公司,当初姑姑的工作甚至是母亲介绍的。
要说有前程,谁比谁还不一定……
整个饭桌的气氛诡异起来,母亲攥我的手更用力了。
“鑫啊,你最近工作咋样?”
我听上首的爷爷语音里带着笑问父亲,父亲似乎终于找回了主场话题,变得眉飞色舞,唾沫横飞。
“一切都顺利,董事长给我说明年表现好就升职加薪!”
父亲在的公司是个外资大厂,一年的工资虽然不及母亲的一半,也有个几十万。
“不愧是我儿子,争气!”
我朝奶奶看,她脸上的褶皱“唰”一下抚平了。
明明升职加薪还没着落,奶奶却同父亲成了已经董事长一样神气。
姑姑找了个去洗手间的理由暂时离席,我明白她不仅是针对我,她也看不起我父亲。
当年爷爷奶奶逼她辍学打工养我父亲读书,结果我父亲不争气,只不过读了个高职,多亏遇到我母亲。
我也去了洗手间,在门口却听见姑姑咒骂我爸败絮其中烂泥扶不上墙,爷爷奶奶瞎了眼了把他当个宝。
我抿着嘴,不由自主点了点头。
确实是。
也就爷爷奶奶拿他含嘴怕化,捧在手心怕摔了,只因为他是独子。
一场家宴在一声声客套的恭维中尴尬结束,我和母亲一人一边架着父亲的两只臂膀,醉酒中的父亲仍在口中高声自语。
内容无非就是吹嘘自己在公司里,如何的劳苦功高,如何的备受重用。
跟在后面刚出旋转门的姑姑在一旁添油加醋的讥讽,乐得看我糊涂父亲挥舞两只手臂,把我和母亲折腾的够呛。
我知道她喜欢看我们应接不暇的模样。
父亲两腮嫣红,眼睛半闭半睁,张牙舞爪地像只螃蟹挥舞蟹螯。周围人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我和母亲身上,像是看舞台上的小丑。
我向母亲那边张望,母亲只低着头,掩盖在那头乌发中的耳朵红得惊人。
我听她小声说:“丈夫,咱该回家了。”
我咬住嘴唇,竭力压下把父亲的胳膊甩开的冲动。
母亲总要顾及父亲的面子,而我总要顾及母亲的面子。
面子面子,顾及着面子的人总要打掉牙往肚里吞。
我深知母亲就是这样的人。
我架着父亲的半边身子,他沉得像山,而我像被压在这山下的孙悟空,动弹不得。
我家在小区的最里面,好容易摁着电梯,走廊上的声控灯就亮了起来,父亲还在对自己的功绩滔滔不绝:“公司要没老子,早他妈完蛋了……”
我知道接下来一定会上映全武行,我脑中不由浮现了上一世的情境。
自尊心受挫的父亲拽着母亲的头发,使劲儿往墙上撞,那雪白的墙上留下一点点血色的红梅,透进墙里,铲不掉了。
我这样想着,对架着父亲另一胳膊的母亲哼哼了句:“妈,我有点头疼。”
我故意抽了抽鼻子,母亲脸上浮现出一层担忧,说:“回家吃点感冒冲剂。”
我踌躇一会儿,才斟酌着开口:“我上次喝完了最后一包,家里好像没药了。”
“我去买。”
母亲将肩膀一松,推着父亲上了床,我抬起父亲的两条腿,挪上去,两只胳膊酸痛得呜呜作响。
“啪嗒”门落锁的声音响了。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。灯光罩下来,父亲的影子直直吞没了我。
我看着他因为酗酒而涨红的脸,心脏跳动越来越快,根本刹不住闸。
他会打我吗?或许这一次会跟上一次不一样?
我支走了母亲,他的火气或许没那么大了。
我朝床上不住地望,一点点轻手轻脚地往屋子外面挪。父亲眯着眼,呼呼喘着粗气。我没有出一点声音,他那双细线一样的小眼睛还是对上了我的。明明已经准备好了挨上一顿打来换取证据,我却僵在那里,各种各样的念头都来了。
他会打我!我得跑!
他也不一定会打我,毕竟这是我重生了。
谁说一世一定跟上一世一样呢?
我的脚踩在了棉花上,父亲猛兽出笼般的吼声猛然撞击着耳膜。
“兔崽子,给我站住!”
不能站住!他会揍我的!
快——跑——!
我朝门外一窜,反手关上门,额头麻麻的,太阳穴生疼,心脏像是快要吐到口腔“咔嚓”一下被咬碎一样。
门“咚咚咚”响个没完,我抵着门,从门框上摸到了钥匙,手却是哆嗦着,怎么也插不进锁眼里。
得快点!再快点!不能停下!
我脖子上那一圈青紫和额头同时烧了起来,我死死用尽力气抵住门,两条腿酸溜溜的,没一会儿就面条似的了。
门“哐叽”一声巨响。
父亲走得摇摇晃晃,方向很明确。他的身躯挡住光线,“啪”一个耳光甩过来,我听见了耳朵的嗡鸣,头皮被人整个撕开一样。我眼前一片雪花点,如同老旧的坏掉的电视机屏幕。
我感觉自己的灵魂飘飘忽忽,头脑里只剩下了两句话
——完了!
——要被打死了!
“兔崽子,有本事你给我长长脸……”
父亲的恫吓声像狮吼,我听见自己的脑袋“咔嚓”一声,断了档。
渐渐的,眼前的画面与我六年级的经历重合了。
十几年前,我们一家住在简易楼里。那时候家里没钱,我的衣服都是捡的表哥穿过的衣服,那时候他还活着。
姑姑时常救济我们,我最喜欢她带来的冰糖葫芦,裹着晶莹的糖,上面撒了芝麻,一口咬下去酸酸甜甜。
我几乎是每天都盼着姑姑来我家。
奶奶爷爷对表哥简直当成了个宝,他们会包很多压岁钱,表哥拥有厚厚的一层,我只有一张薄薄的蓝纸。
父亲跟着母亲结婚有了城市户口,计划生育政策执行,反而吃了亏。
父亲骂我是赔钱货,母亲抱着我,他举着拳头砸向我们,“呼呼”生风。
只是因为母亲生不出来男孩,我们都成了出气筒,他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,越喝越上头,我和母亲挨打的频率从一周几次变成了每天都有。
每次母亲弯着腰两只胳膊紧紧搂住我,我都恨不得拿刀捅了他,一了百了。
我的胳膊常年青紫,撸起的袖子都会箍疼我的皮肉,都是母亲拿着蘸了酒精的棉棒一点点给我擦拭开上面的血迹。
直到有一次,父亲一连七天未归,母亲的工资已经是父亲的一倍多。母亲给我做了很多好吃的,还买了田园鸡脆堡的超级套餐。我已经上了初三,住校,一周回一次家,这次放的五一七天是我最舒心的日子。我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,也不想管,只将那句话混着怒气喷出来:
——“妈!你必须离婚!”
母亲闻言怔怔地看着我,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,拍着我的背将我搂进怀里。
没一会儿我就感觉后肩的衣服湿透了,腻乎乎的像一层皮肤。
傻孩子,我听她说,我不能自私,那样你就没有完整的家了。家丑不可外扬。
姑姑曾经专门来过一次,拉着他到别的屋里去谈话,我舔着糖葫芦上的糖,甜滋滋的。可没一会儿,“噼里啪啦”一阵乱响,脆的钝的呼呼啦啦全涌进耳朵,糖葫芦也折了一半。姑姑捂着脸哭着跑出来,父亲没一会儿凸着灯泡眼出来,“哼哧哼哧”呼着气,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还在打颤,咒骂着:“不过是个泼出去的水,还管着我的事儿了!来一次打一次!”
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了表哥的衣服穿。
我抱着头,父亲的拳头一下子砸在我的左肩膀,我眼前冒起了金星。
“那娘们不就是有几个臭钱供我使使,嫁鸡随鸡嫁狗随狗,我是一家之主,好的都应该是我的!”
我随着他的话接了下去。
你那臭小子哥哥体弱多病早死了,也是你姑姑她活该!呸!
我脑子里一会儿全是哥哥,一会儿全是姑姑,奶奶拉着母亲谈的话也冒了出来:
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,他脾气大点,你多担待。”
和奶奶谈完话后,正巧姥姥打了电话来,我躲在门外,透过那一层缝向屋里看。
母亲抹着泪,说话声音除了有点哑外都正常,她就这样边哭边微笑,挂断电话后,将脸埋进了掌心,肩膀一耸一耸的。
世界天旋地转,我分不清日子是何时了,但——
‘呸!’
我在心里暗骂,火气突然冒出来,头皮一阵疼痛,紧接着是钝钝的抽丝剥缕的疼,我眼前一黑。
我替母亲挨了这份打。
我突然有些自豪,随即又担心起来。
母亲回来看到我,会不会又哭了?老东西还会打她。
我不禁祈祷起来:
妈妈,你可千万别回来啊。
那一晚母亲回来的很快,父亲呼呼大睡。
我仍记得母亲颤抖着紫色的嘴唇,那两片唇抖着,在我的脸上胡乱吻着。
母亲睡着了,我将竖在无线充电器上装着充电的手机攥在手心,里面父亲打我的录像完整地记录了下来。
玫瑰花的刺隔着一层塑料膜,红色的带子系成了蝴蝶结的形状,我口袋里还装了一个平安果。今天是周末,还正赶上圣诞节夜。
太阳特别的毒,我却身上冷飕飕的,转身向一边的大乐透彩票站点去了。
上一世我整个学期都是在学校和家中往返,没有住校。
我记得七月六号我拖着行李箱拧开锁,家里只有母亲一人,衣服都被她从衣柜里一件件丢了出来,满地满床全是衣服和散开的鞋袜,她的脸底色是白的,青青紫紫像是涂上的滑稽油彩,我抱着肩膀浑身发冷,转而跑向书房,地上也是一片狼藉,巴掌大的碎纸屑花花绿绿,我才知道那是一张张撕碎的彩票。
也就是那时起,我才知道父亲对彩票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。
投资超过我,期望值也超过我。
那一天吃饭时,母还收到了一条短信,我不知道是什么,但她头一次在我跟前呜呜大哭着冲向自己的屋子。那一晚,她房间里的灯没灭过。
上一世如同我只翻开了一册书的部分,而另外的一部分要用这一世来见识一下。
我买下了7位数的大乐透,等待着周末的开奖。
我隐隐约约觉得,家庭不幸总是关于钱的缘故。
今天是六月十五号,离我被父亲掐死还剩下一个月零八天。
暑假回家的第一天,天气正好,因为昨天刚下了小雨,暑气不是很大。
我拉着行李箱,好似里面有千斤重。
今天妈还会翻来覆去找东西吗?
是因为钱吗?妈应该不缺钱。难道是什么贵重物品?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东西?要不她怎么会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呢?
但如果是钱的话,也好办了。
我拉着行李箱杆子的手攥紧了,手心里全是汗。我抬头望着自家合上的窗帘,深吸一口气进了楼栋。
家里狼藉一片,母亲的牛仔裤是我进房间的第一件拦路虎。我缓缓吐纳一口气。
上一世的时候,我只知道躲避事情。我不想有任何的麻烦事在身上,也不想主动挑起任何事端。但这一次不同,我必须活着。我要活着见到秋季的太阳,我要活着见到以后每一天许许多多的日出日落。
我推开虚掩的门,母亲正跪在地上把衣柜最下层抽屉里的衣服一件件掷出来。
“妈,你在找什么?”
我的嗓子很紧,紧到像一根拉紧的弦,吐出来的声音干涩沙哑,声音也很小。
“没你的事,回屋去。”
母亲仍然埋头翻找着衣服,声音的音色却是和我差不多的。
“妈我和你一块儿找,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快些。”
行李箱的杆子早被我丢下了,发出“嘭”一声闷响,母亲垂着头,我抱住她,她将我推开。
事情有些不对了。我想。
妈从来不会推开我,她虽然严厉,但……
我看她半垂着头,长发挡住了她的脸,我看不清她的表情,但一滴明晃晃的水珠,顺着她西装的衣领滚到胸口。
她哭了。
我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,像被人打了一拳。
妈从来不会在我面前哭,从来不会,从来不会……
新书推荐
-
 红衣女人
赵眠眠 | 完本
红衣女人
赵眠眠 | 完本
-
 大龄女博士月薪一千九
樱桃和小玉兔 | 完本
大龄女博士月薪一千九
樱桃和小玉兔 | 完本
-
 我走过你走的路,我和帅哥相逢
彩云 | 完本
我走过你走的路,我和帅哥相逢
彩云 | 完本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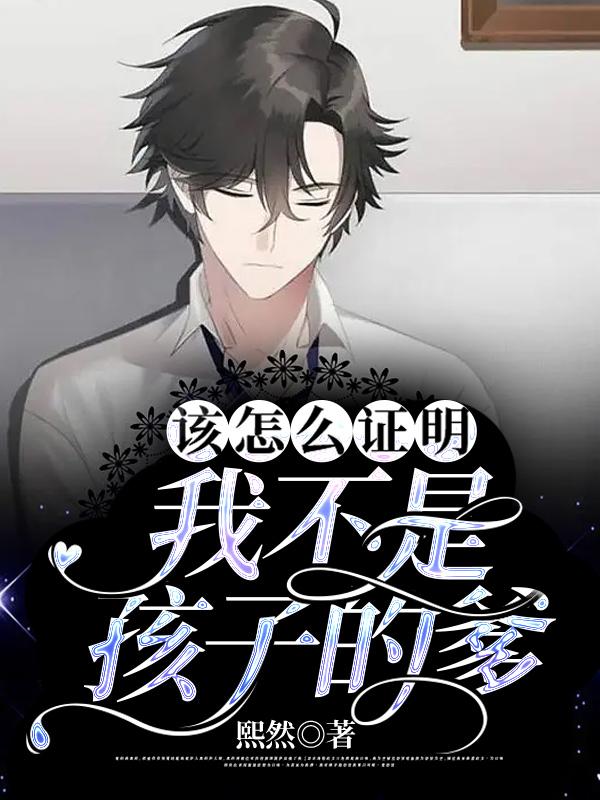 该怎么证明我不是孩子的爹?
熙然 | 完本
该怎么证明我不是孩子的爹?
熙然 | 完本
-
 五年婚姻我赢了老公的白月光
爱吃小葡萄 | 完本
五年婚姻我赢了老公的白月光
爱吃小葡萄 | 完本
-
 健身房里暗藏玄机
离人泪 | 完本
健身房里暗藏玄机
离人泪 | 完本
